故事的下半段:讲述与寻找
——彭争武诗集《寻找》序言
作者:燎 原
读罢彭争武的这部《寻找》,大脑中突然冒出一句话:“一个人绝不只是他自己。”首先这是基于诗集的内容和作者凸显的特殊身份,既而是由作者所代表的一个特殊人群:已成为珠三角地区活跃变革力量的新一代移民。他们无一不是当初为那片“新大陆”所召唤的外省青年,每个人都具有相应的文化教育背景,因而满怀闯世界的胆识与自信。在充满机遇与压力的异乡,大部分人都以广义打工者的身份,从低层干起,继而凭借超常的拼搏浮出水面,而有了城市主人的身份。他们参与并见证了一座城市发展奇迹的创造,也在最富能量的年华成就了自己。进一步地说,这也是改革开放四十年来,覆盖了中国经济发达地区一支最活跃的人群。尤其是在彭争武身居的东莞。
但这其中的每一位,却无不伤痕累累,在其群体编年史上留下了一长串的故事。这一故事的上半段,已由此前风起云涌的“打工诗歌”代为讲述。如今,当他们已经实现了上述身份的转换,其此在的心灵行迹又是如何?彭争武则用这部《寻找》,承担起下半段故事的讲述。
从语态上讲,所谓的“寻找”,是以过来人已趋平和的心态,对于自己过往岁月的盘整与梳理。那仿佛是咆哮的海潮退去后的一次回望,或一台大戏终了后突然的人群散去,刚刚还置身其中的作者,突然处于莫名的幻觉状态——刚才那场大戏是怎么发生的?剧中的角色们都去了哪里?我自己又是怎样走过来的?现今的我,是否自己当初渴望的那个我?如果不是,“我”到底又是什么?或进一步地说,人到底又是什么?这一连串的疑问,遂转入那一著名的哲学追问:我是谁?我们从哪里来,我们到哪里去?对于这一追问,相信每个当代文化人都不陌生,但只有具备了足以触动灵魂的经历,它才会成为一个真切的个人问题。而随着这一追问,压缩在生命史中密集的信息便不断发出声音,并以刚才的那场大戏为中心持续回溯,将自己的刚才史与史前史,个人史与群体史贯通起来……我正是在这一时态上,想到了“一个人绝不只是他自己”。
而彭争武的群体史,当然是与他一起走过来的那一人群;其史前史,则是他这只风筝线头的始端,其乡间的父母和祖居之地。
也只有在这一基点上,一个人才打通了自己的来龙去脉,他关于自己“新一代移民”故事的讲述,才有了区别于上半段的纵深感。
这一叙事的突出特点,首先是它的扁平结构。尽管导入这样的纵深地带,它却摒弃了宏大叙事的取势。近百首相对独立的诗作,似是不经意地贯通为一部长诗,但其间并无怒潮排空式的激烈隆起。写作的触发点虽然缘之于刚才史,却不再重复那些痛苦的故事,不再于那些已形成热点效应的题旨上借势追加,而是将这一核心区块打散,使之以时隐时显的碎片,唤醒并调动其人生的相关记忆。隐约或凸显其间的少年史、青春史、奋斗史,以及与之密切关联的乡村史、梦幻般的新兴城市史,却以具体的个人标本,勾勒出一个时代的历史性变迁。
——尽管这非常重要,但作者并不满足于完成这一故事的讲述。使他执念不舍的,则是其中更深层次的问题:我是谁,或人是什么?这才是与其经历相匹配的、真正属于他们的问题。搞清了这个问题,也就自然搞清了我该向何处去。那么,我到底是谁呢?这却又是一个无解的发问。因为每个人的“我”都有阶段性,不到最后时节就存在着变数,甚至是意想不到的巨大变数。这正是变幻莫测的人性奥秘。但作者虽然无法确切回答,却以特殊的叙事语态,就自己眼下对于这一问题的体认,做出了间接表达。这是一种外在平和,内部却由温热、疼痛、坚硬、冷漠所交织的叙事语态,其象征意味虽还够不上“我承认,我曾包经沧桑”,却在极为相近中表达出这样的潜在语义:世界的进程原本如此,你既无须在逆境中顾影自怜,悲愤难当地去谴责什么;也不必为某种暂时的成功所陶醉并感激什么。
对于一切到来的,无论你愿意还是不愿意,你都只有接受,并与你不甘接受的抗衡、角力!至于你能否最终胜出,尚还有待继续走着瞧,而你所能做的,就是在人世的沧桑中迷失了自己(“我忏悔我的老练/ 还有我的圆滑”),又始终在寻找自己的——那个人。这便是彭争武对我是谁,以及人是什么的结论,也是他寻找到的个人真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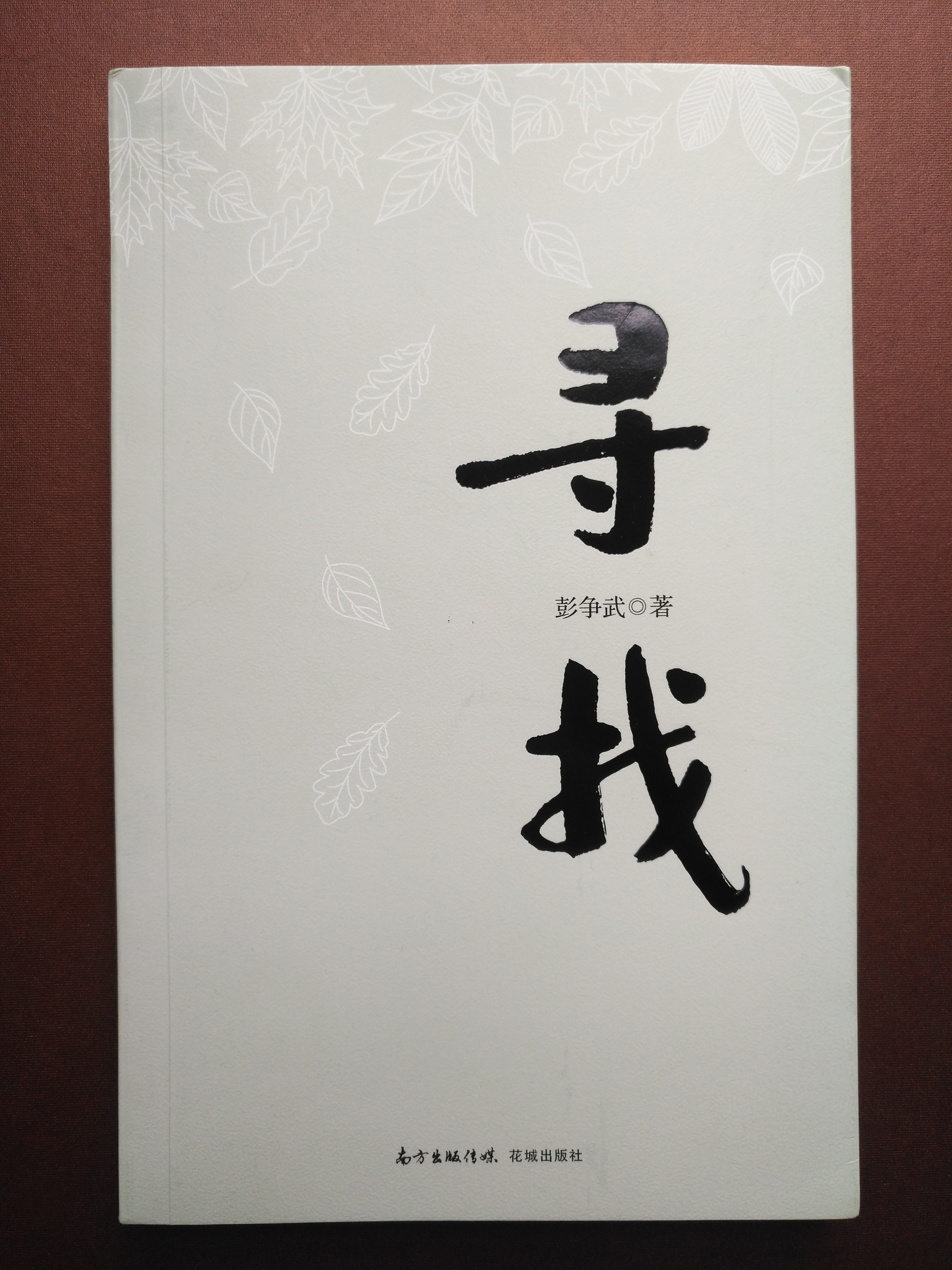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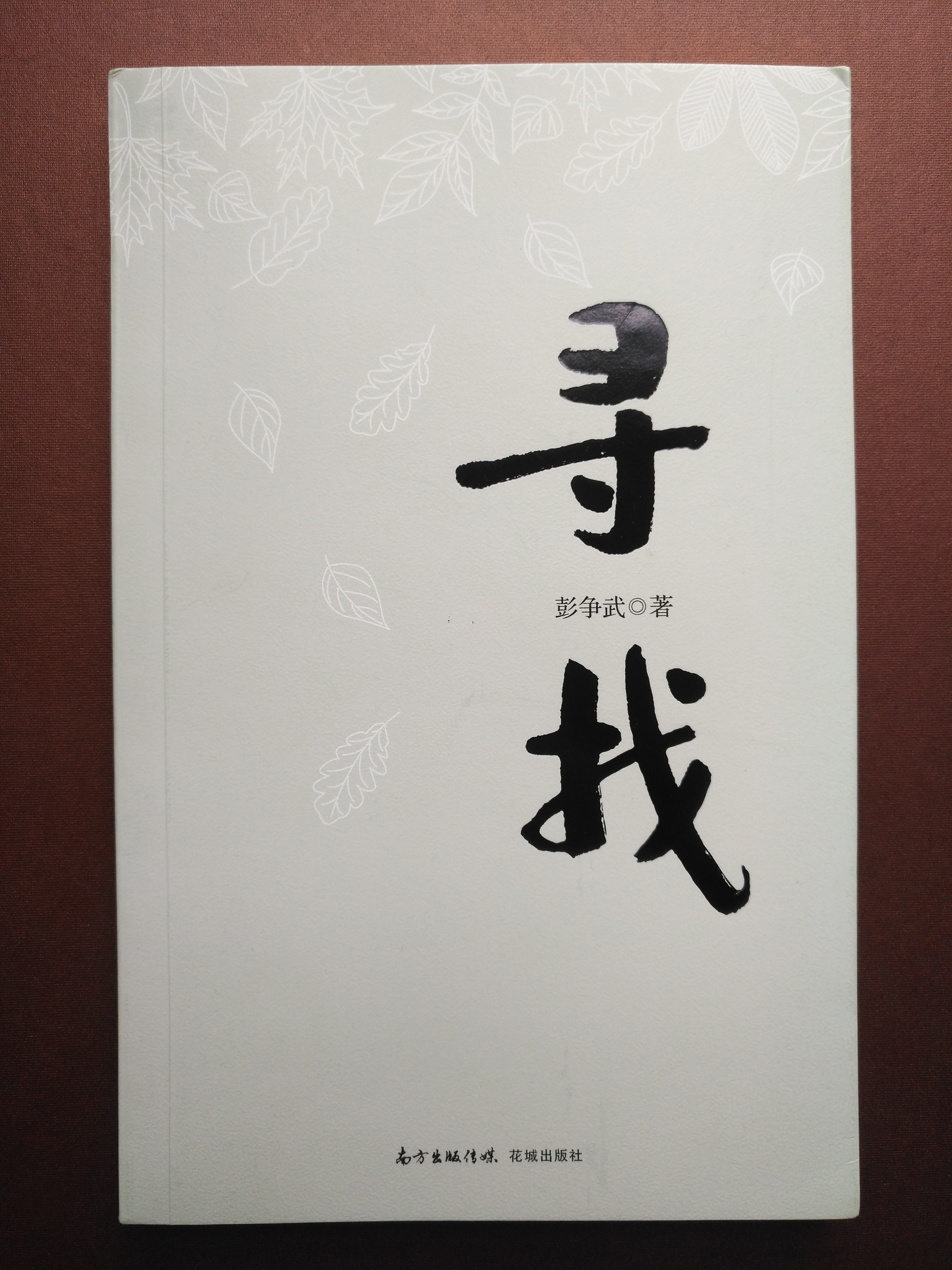
也正是基于这一深度寻找,这部诗集不时闪现出让人惊奇的个人真理。诸如他在《车祸现场》中的发现:“你看吧,车与车,最温暖的交往/ 莫过于:擦肩而过”“贴近的方式:毁灭/ 贴近的代价:毁灭// 铁的事实/ 就是废铁”。你当然会明白,这是他关于人际交往的冷酷隐喻和指认,显然不同于神仙们冠冕堂皇的说教,但它不正是说破了真相的一个极端真理?它提醒我们这样一个事实:在一个内部构件经历了空前颠覆与再造的时代,既往所有的公共真理都面临着经受个人的重新体认。
与之相反的极端真理当然不适应所有人,但却适应与之感同身受的一部分人,乃至一大部分人。从另外一个角度说,诗人的天职绝不是重复既有的大道理,而是从其所处的时代不断获得个人发现。唯有如此,才可还原世界的复杂本相。
而在这种冷酷语态的另一侧,则是疼痛的温热,并泛动在他群体史与史前史的叙事空间。比如“寻找少年大哥”“子美的死”……更包括大量涉及故乡的情绪:比如他有时看到街边的一棵树,就觉得它像家乡的一位熟人;看到街边一位行人,又觉得他像家乡一棵熟悉的树。以至每每半夜醒来,都“心口隐隐疼痛”(《家乡》)。尤其是不断出现的他与父亲之间的叙事:“我给家里写信/ 我写了三个钟头/ 我写了六个字:/ 父亲/ 我睡不着”(《写信》)。再比如他与父亲一个长途电话的特写:父亲的声音越来越轻,语气越来越慢,内容中不再有那些自己身体和村里提留集资税收的糟心之事。这让他多了一份意想不到的欣喜。但接下来的事情同样让他意想不到,挂电话的一瞬间,父亲的咳嗽竟然破空而来(《晃荡的话筒》)!——没错儿,父亲如此强憋着咳嗽的心平气和,显然只是为了让远方的儿子放心。
从给父亲信中的“我睡不着”,到父亲电话中的这个细节,你当然不会感受不到,人生有着多少难熬之事!但两人却转换出一种共同表情:事实上的或力图表现出的心平气和。
这就是岁月研磨的结果啊。而正是这种研磨,又造就了彭争武诗歌的语言形态,他完全剔除了叙事中的煽情、滥情元素,以尽可能简朴、节制的文字,使叙事趋向精确,以逼近生存中那些足以撼动人心的真实气息。而在诸多关节处,那些冷不丁出现的,充满佯谬、悖论却堪称精彩的“个人真理”,亦是这一造化的结果。从本质上说,这些佯谬与悖论完全与生存同构,它们原本就隐匿在现实中,只是被脑洞大开的作者发现之后提拎了出来。
那么,这一切是否都意味着,人被岁月盘整得已没有了抒情欲望?但在《活着》一诗中,他对年轻时作为染匠的父亲的这段描述,却泄露出他深藏在心灵中的绚烂:
父亲把自己丢进染缸
一排排白布迎着黎明
就依次展开了
波浪式的白布
如广阔而空旷的原野
世界上的斑斓
就从父亲的光脚下一个足印
叠着一个足印延伸
威海蓝波湾
2018.3.4
 本网声明
本网声明 邮箱
邮箱 | 读书频道
| 读书频道



